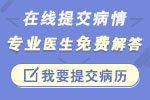首页 > 病种新闻 > 内科 > 中医 > 行医甲子 大医圣心 ——记医学大家曹泽毅的医者之心
行医甲子 大医圣心 ——记医学大家曹泽毅的医者之心
面对医学大家、优秀妇产科大夫曹泽毅教授,很难准确猜出他的年龄。从面容上看,他当然已经是个老人,一头银发,眼睛不再清澈但眼神柔和,和大多数家庭里含饴弄孙的老人一样。
摘要:
面对医学大家、优秀妇产科大夫曹泽毅教授,很难准确猜出他的年龄。从面容上看,他当然已经是个老人,一头银发,眼睛不再清澈但眼神柔和,和大多数家庭里含饴弄孙的老人一样。但他确乎不是一个在家里散淡时光、颐享天年的老人,他几乎每周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北京一家医院里看诊,并且经常亲临手术一线,操刀大手术——“这几天我天天都在动手术。”他乐呵呵地告诉我们。
耄耋之年,医者之心不已
“我有过很多值得骄傲的头衔,但不论走到哪儿,都会记得自己是一名妇产科医生。”2007年在川大华西医生115年华诞上,作为杰出校友代表的曹泽毅曾这样说:“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够在临床上再待20年。”
如今,将近10年过去了,已经84周岁的他,果然行以践言,依然壮心不已,操刀手术。
没有人能质疑这位老人的一线操刀能力和精力。年轻大夫们跟着曹泽毅做手术,都反映很有压力,因为随时得紧绷神经,对手术进程做出反应,“你不能耽误我的时间。”他说。曹泽毅的意思是,在手术台上一分钟都不能浪费,面对各种情况**快速反应,一步到位,这是对病人最基本的负责任态度。“否则我就急了。”曹泽毅说这话时完全不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而是一名活力四射、随时备战的临床大夫。
关于这点,曹泽毅身边的年轻大夫都深有感触,并对他旺盛的精力自叹弗如。在很多需要耗时7、8小时的大手术里,他可以一直站立,不喝水、不休息。而协助他做手术的年轻大夫反倒要轮流下去歇口气。这样不累吗?“当然是累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全神贯注的时候,他的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都会减慢。”曹泽毅科学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累”。实际上,但凡做过大手术的医生都知道,在一台超过5小时的大手术里,支撑主刀大夫能够一直保持全神贯注的状态,除了需要良好的身体状况,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医者之心。
谨记父亲教诲,传承医者之心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曹泽毅刚刚进入医学领域时,曾任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上世纪40年代优秀的内科传染病专家的父亲曹钟樑就曾告诫他:选定了做医生,就要明白两件事——一是做医生非常辛苦,一辈子不会轻松;二是做医生不会成为有钱人。“治病救人就不能是一件赚钱的事。”父亲告诉曹泽毅。大概是父亲榜样的力量,也大概是父子之间的深厚情感,这两条朴素的叮嘱曹泽毅记了几乎一辈子,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里,曹泽毅凭卵这两条信念淡然走过了无数坎坷、苦难的时光。
上世纪60年代在四川医学院的家属楼居住过的老人们都记得,经常在半夜时分,医院的那位负责打杂的老太太会跑到家属楼下面大叫:“曹医生!曹医生!”,大家都习以为常,知道是医院妇产科手术台上又有紧急情况,曹泽毅又该去加班了。几分钟后,便能听到曹大夫急促的下楼声音。
对于曹泽毅和做药学老师的曹夫人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平常时光。
其实曹泽毅并非天生热爱医生这一职业,他从小热爱飞机、火车,这些机械模型,而且喜欢动手制作,所以一直认定自己是个学工的料,相反弟弟因为聪明、活跃,被全家人认定是父亲的接班人。可没想到1950年初,四川刚刚解放,到处是应征入伍的热潮,弟弟拉着曹泽毅去应征,结果哥哥没有被选上,身材高大的弟弟却被录取,离开家到了部队。1951年,心里不服气的曹泽毅又去应征,但是父亲早就“盯”上了他。并生平第一次动用自己的人脉,给征兵办负责体检的人打了招呼:“我这个孩子身体条件不好,不能当兵。”于是,曹泽毅“合理”地体检不合格,再一次落选。同年,曹泽毅遵从父母的期望,进入华西大学医学院做了一名医科学生。
作为一名从心底里热爱医学的医学专家,曹泽毅的父亲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衣钵,而且曹泽毅的母亲也有合理的情感需要:两个孩子,总要有一个留在身边吧。
但曹泽毅认为自己进医学院也并不是**因为父母的安排和要求,对于他来说,父亲是一名优秀医生,医学是一个非常亲近的朋友,从小就在医院环境长大,对医学“有天然的亲近感”。
对于曹泽毅而言,人生更重要的是对于科学的态度。从小他的父亲就对他一直强调对于学习和工作的认真和负责任态度,有了这一人生原则,无论在任何领域,都会得到学有所成的喜悦。
曹钟樑对于曹泽毅来说,不仅是一个父亲对于孩子的言传教育,更重要是作为一个严谨知识分子的身教,尤其是曹泽毅在成为一名医生之后,更能体会到父亲给予自己各种教育的弥足珍贵。“他教育我要认真,要对工作负责,要甘于医生的清贫,这些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
上山下乡,治病救人,不忘医者之心
1956年从四川医学院毕业的他作为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师,因为父亲是经常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培训、进修的机会。但有一种“机会”却经常降临到他身上,那就是到艰苦的农村及山区进行“上山下乡巡回医疗”。1958年,国内第一批“上山下乡巡回医疗”,曹泽毅就作为服务还不错的年轻医生代表被选中,带队到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进行巡回医疗。
木里地处四川西南边缘,交通不便,设施落后。曹泽毅和几名实习医生要先坐汽车然后再步行两个星期才能到达木里。当时木里县城里只有县政府、一家医院、一家银行这三个机关。因为都是牧区,许多病人的救治需要从驻地骑马过去,为此曹泽毅学会了骑马,还学会了扛枪射击——因为沿途偶有土匪出现。记得有一次一位藏族老人阑尾穿孔,情况十分紧急,需要立即手术。接到呼救电话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天黑之前肯定不能到达病人那里,尽管曹泽毅知道夜晚出行在藏区多么危险,但是他二话没说立刻拿起药箱,披上袍子,一个人骑上马、挎上枪赶往牧区。等到了地方,看到病人和环境,曹泽毅当时就傻眼了:现场只有一口蒸饭的锅和两把钳子,没有任何的手术设备!而曹泽毅带来的药箱里也只有一根打腰麻的针和一点麻药。可手术**要做,否则病人只有死路一条。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啦:“医生要救人,方法你自己决定,条件自己创造,这是医者心。”
于是,曹泽毅叫人马上到镇上小卖部买了片刮胡刀片,充当手术刀。术手术缝针的针和线都没有怎么办?妇女们的缝衣服的针线煮一煮用上!天已经黑了,照明也没有怎么办?赶紧现场找四支电筒,对着病人齐齐打开……就这样,手术完成,老人获救。曹泽毅在当地一下子出了名。
“这不算最有意思的。”时隔近60年,曹泽毅虽然记得清晰,却毫不激动,恍若聊**故事。他觉得最有意思是有一次在牧区,一位藏族妇女肚子莫名其妙地大,曹泽毅一看,就知道是她肚子里长了瘤子,仔细摸诊后,判断是个良性瘤子,便当机立断给她手术取出了瘤子。没想到这位藏族妇女觉得这一切都太神奇了,就把瘤子要了过去,拿到大街上摆着让人参观了三天。
对于曹泽毅来说,在藏区艰苦的工作经历**的收获,除了让牧民们重获健康,更重要是自己有了大量的临床机会,积累了难能可贵的临床手术经验——就像与他同时代的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曹泽毅丝毫没把苦难在情绪上去夸大,而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的专业工作上。即便在专业上的帮助伴随了境遇的窘迫和待遇的不公平,但是,科学、专业、工作,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怎么办呢?我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自己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已经让我足够高兴了。我有时甚至庆幸自己的出身没有那么好,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下乡临床机会。”
这种临床机会的确大量给予了曹泽毅这样政治上靠边的人。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四川许多农村地区的妇女都患有子宫脱垂,于是,政府派医疗队下乡免费治疗。生病的妇女们被集中到乡医院等待治疗。曹泽毅带着一个学生到了现场,学生一看就犯难了:“天哪!这么多病人,曹老师怎么办啊?!”——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让曹泽毅都感觉很难常规地处理。他沉思了片刻,马上想出了解决方案:把妇女病人们集中到乡里的小学,把小学教室里的课桌摆放成排,一排十个,病人们一人一张桌子躺上去,然后曹泽毅开始一个接一个连续用局部麻醉做手术,上午做10个病人,下午再做10个,间或还有增加。完全不休息,连续作战……
这些匆忙的、仓促的,甚至是狼狈的时光,对于曹泽毅来说,没有丝毫的怨言,对于一个全心全意在医学专业领域的医生来说,病人们感激的目光,每做完一台手术抹掉的汗水,都是这些经历的奖赏和馈赠。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从1956年曹泽毅大学毕业一直持续了8年的时间,直到1964年他作为国内第一批统招硕士研究生,考入北京医学院深造。
出国进修,国外同行从质疑到刮目相看
也许这就是人生经历的公平。当毕业20年后,曹泽毅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去到医疗先进的发达国家瑞士,他再一次确证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当年那些洒在临床一线的密集的汗水是多么值得!
作为“文革”结束后几乎是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的人来说,曹泽毅显然在理论和实验上的基础是不够的,但他的临床技术却是优秀的,这也为他争取了机会。当他第一次给瑞士巴塞尔大学妇产医院的院长做手术助理时,就被这位手术专家发现了他**的地方。在独立完成一台手术后,院长邀请曹泽毅去指导医院的年轻医生们做手术。
起初当然得不到信任,国外同行都质疑曹泽毅:这位国内医生会有手术经验吗?而且当时他的语言关还没完全过,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而周围都是来自德国、瑞士、丹麦、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出来做学术交流的医生,曹泽毅在其中十分不起眼。曹泽毅在瑞士的第一次手术带的是一名英国医生,对方一点不掩饰对他的不信任感:“你能带我做?”曹泽毅以东方人的做派,平静地回答他:“咱们看看吧。”英国医生更不服气,问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既然你带我做手术,那请你告诉我,你切过多少子宫?”曹泽毅还是很平静:“或者你可以先告诉我,你做过多少子宫切除的手术?”年轻的英国医生非常骄傲:“15个。”曹泽毅听罢,笑了笑。对方不干了:“曹医生你笑什么呢?”曹泽毅拍拍英国年轻人的肩膀说:“我不记得我做过多少例这样的手术了,如果你非要我回忆,那可能有一万多例吧?”“这怎么可能?” 英国医生急了,“怎么不可能呢,因为我几乎每天至少都要做4-5例。”
信任当然不能光靠说,还得靠做来争取。曹泽毅最终通过自己的手术临床水平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和欣赏。
精湛的外科技术,也为曹泽毅获得了在实验方面的进步:“你们教我做受体实验,我教你们做手术。”——交流学习显然非常成功。在两年的时间里,瑞士巴塞尔大学妇产医院的中心实验室的下午、晚上、周末这些时间都对曹泽毅开放,让他一人在里面尽情做实验。“那些试剂太贵了,在国内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两年下来,曹泽毅用瑞士的实验室写了一篇关于妇科肿瘤受体的论文。“可谓受益匪浅。”他说。
要创新,也要传承
或许是因为父亲曾经是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的缘故,对“华西大学”这四个字曹泽毅充满了怀念之情。在他进入这所学校就读的第二年,学校就根据国内的大学调整风潮改为了“四川医学院”,这一名称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
1984年,刚刚从瑞士、美国留学归来不到一年的曹泽毅因为学院民主选举校领导而“连升五级”,行政职位上从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一举升到四川医学院正院长的职位,这一结果不仅惊到了曹泽毅本人,连父亲曹钟樑也懵住了,老人甚至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找到卫生部,告诉主管领导:“曹泽毅做不了正院长,知子莫若父,他做不了!”但上级领导既没有问曹钟樑为什么“不能”,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尊重了民选结果,任命曹泽毅做了四川医学院院长。
曹泽毅在任职院长期间有过许多改革创新的举措,诸如他是第一个在高校把电化教学搞起来的学校负责人,而且他还在学校第一个搞起了远程电视,学校中心闭路电视系统的视频,每一个教师在家里通过电视都能看见。这在当时高校的管理上无疑是一项创举。
而曹泽毅影响**的改革,则是大胆提出要把四川医学院改回“华西大学”。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经努力,四川医学院暂时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并带动了国内一大批医学院改名为“XX医科大学”。
说起这段往事,曹泽毅至今还有点遗憾:“我应该坚持改为华西大学”就好了——他的遗憾,大概是源于一种对于父辈的敬意,一种科学不仅应该创新,也应该传承的理念。这些,是当年那位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曹钟樑先生给予他的。
“华西大学”四个字,几乎概括了曹泽毅对于医学、对于科学的所有寄托,那就是钻研、认真、负责。他记得1981年,在瑞典巴塞尔被授予博士学位时,被邀请在一本厚厚的纪念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翻看了一下,厚厚几百页的纪念册,他是第一个国内人。在那一刻,他心里默念的是“华西”二字。
曹泽毅关于医学的Q&A
曹泽毅,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卫生部副部长、国内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现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璞至医疗专家委员会主席、航空总医院名誉院长、国内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妇产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M.D.Anderson肿瘤医院客座教授。
Q您觉得作为一名好医生,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
A首先理论基础要好,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学历,但是最起码是大学毕业,或者比较好的大学,因为系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一样的,这是基础。第二个就是他的临床能力。当医生也要有悟性,尤其是外科医生,要善于总结经验,不仅是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都十分重要。另外医学跟艺术是分不开的。外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很多外科医生都懂乐器,像我自己就热爱拉小提琴。
Q像您这样一位泰斗级的医生,您觉得带学生更重要还是临床的每一台手术更重要?
A我认为做医生首先服务不能丢掉,有机会还是要多接触病人和手术,除非你自己不想做了。我个人还是愿意继续做一些临床的工作,这也是为病人服务。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带几个好学生。当一个好的老师,不管是教授、医生,只是自己好当然不错,但是我觉得这最多就是人生成就的80%。因为你总有不行的时候,总有过去的时候,所以重要的还是要带好学生,要把你的经验传授给后辈。
带学生怎么带?**把你最精华、较好的教给他,把你在10年20年积累的经验,用一两年的时间传授给他,让他尽快地成长起来,而且在很多方面你要想方设法让你的学生超过你自己,这才行。
一个有名的大夫,或者教授,如果直到你去世的时候你都是较好的,没有学生超过你,我认为那是你的失败。
Q传承还需要有创新,要一代一代发展下去。像您从事的妇产科,是特别受大众关注的科室。妇科病一直存在一个传统的观念:不可知、不可预防。想问您一个专业的问题,如何预防妇科病?
A这个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妇科病是可以预防的,像炎症、感染等,只要平时多注意清洁卫生,重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可以预防的。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肿瘤,只要可以做到定期检查,预防也不难。女性应该一年至少做一次妇科检查,包括做盆腔检查、B超,TCT、HPV检查等。
大多数妇科肿瘤是可以在早期发现和**的,就比如宫颈癌,现在已经明确了它的主要致病原因就是感染了高危型HPV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发现感染了HVP病毒也不是说马上就癌变,还是有个过程,一般要三到五年,长期反复感染HPV病毒,甚至于更长时间才会癌变,但是,这种病毒感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这就需要定期去检查,一旦发现感染HPV病毒感染已经形成病变,只要及时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
Q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妇科癌症发病率高发且有年轻化的现象,作为专家您怎么看?
A这是当前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因为环境的污染、生活习惯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了癌症的增加,就像宫颈癌。90%以上的HPV感染都是通过性生活感染的。现在女孩子的性生活时间都提前了,以前我们不能接受孩子婚前就有性行为,但是现在我们都接受了。可医学研究发现,如果在18岁之前就开始有性生活,她得宫颈癌的概率就比18岁以后要高,因为她的生殖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不过对于HPV感染也不要过于恐惧,因为,80%的已婚男女都会有HPV感染,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要注意的是第一要保持清洁;第二个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心情愉悦,人的免疫力就会增强,就像感冒一样,它也可以自愈。但是,如果病毒已经侵入子宫颈造成病变,那就要治疗了。第三,要定期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现在癌症发病率高了也不完全正确。
Q 关于宫颈癌,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疫苗可以提前预防病发,国内这种疫苗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
A 宫颈癌疫苗已经在欧洲、美国,甚至亚洲一些国家,推广使用了十多年,而且已经被证明确实有效。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建议是没有感染过HPV病毒的女性,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性生活的女性,这种疫苗对她们最有效。所以,专家的建议是对13岁以下的女孩注射该疫苗效果更好。
或许有人问我已经20多岁了,或者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不可以打。我们的建议是你当然可以打,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了性生活,那么打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从来没有感染过HPV病毒的女性,给她注射疫苗,可以生成很高的抗体。如果已经感染过了,就对它有一定的免疫力了,那么抗体就生成不上来了,注射的意义也就不是那么大了。
现在这个HPV疫苗对宫颈癌来说是很重要的,很多国家把它作为政府的免疫项目来做。
但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个人去打当然可以,但意义不大,这个需要大范围的人群打才有意义,才能真正预防和降低宫颈癌的发病。我初步估算过:在国内保守估计,适合注射疫苗的女孩有1个亿,如果全部都满足注射的要求,估计要花几百亿。虽然现在到处都需要用钱,但如果花这一笔钱能够保国内妇女在20、30年以后大大减少宫颈癌、甚至不会罹患宫颈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千秋万代的事,这个钱是值得花的。
如果将来能够在国内这么一个人口大国消灭宫颈癌,在全世界还是很大的事。
Q 对于癌症,中医西医的选择在国内始终是个争论的话题,您怎么看?
A 我个人比较相信中西医结合。不过,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首先要有科学态度。得了癌症要去确诊。然后再从西医角度判断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使它治疗,比如手术、化疗、放疗等。中医对有些治疗是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的,比如帮助病人提高他的免疫功能,这一点很重要。相反西医就不太重视这个,手术、化疗、放疗,一方面有效,但另一方面也破坏病人的免疫力。怎么在保护免疫力的情况下消灭癌细胞,消灭癌症,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般来说早期癌症不管是西医的手术、放化疗,还是中医的保守治疗,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但到了晚期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主张“带瘤生存”。过去西医遇到肿瘤总是穷追猛打,非要把肿瘤去掉、消灭,可最后把病人也灭了。“带瘤生存、治病留人”是中医的一个很科学的观点,现在西医也接受这个观点了。如果能控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让瘤子不再生长,我们就可以让病人带瘤生存,这样不仅可以保住病人的命,而且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 相关标签
相关新闻
- “爱美之心”是美容业兴盛的重要原因2012-11-15
新闻回顾 本周 上周
- 行医甲子 大医圣心 ——记医学大2017-08-09
- 广州美莱获丝丽动能素2017年度指定2017-08-09
- 金戈有副作用吗?专家为你详细解读2017-08-09
- 江西省给医务人员建信用档案2017-08-09
- 重庆市专项救治农村贫困人口大病2017-08-09
- 宁夏:成立出生缺陷综合干预中心2017-08-09
- 在空调房中醒来 小伙子嘴歪眼斜2017-08-09
- 郑州市实施空气污染临时管控措施2017-08-09
- 九寨沟县人民医院首批4名伤员已开始2017-08-09
- 广东医改进入深水区 药企应如何应对2017-08-09